隐蔽的攻击性
夜常反思。
我前两天上豆瓣找到以前的一个观察对象——有一点观察价值但不会成为朋友也不受尊重的人类——将自己的观察记录发给了他。这一部分内容自然不是好话,说是羞辱也不为过,至少对方表示自己受到了侮辱和伤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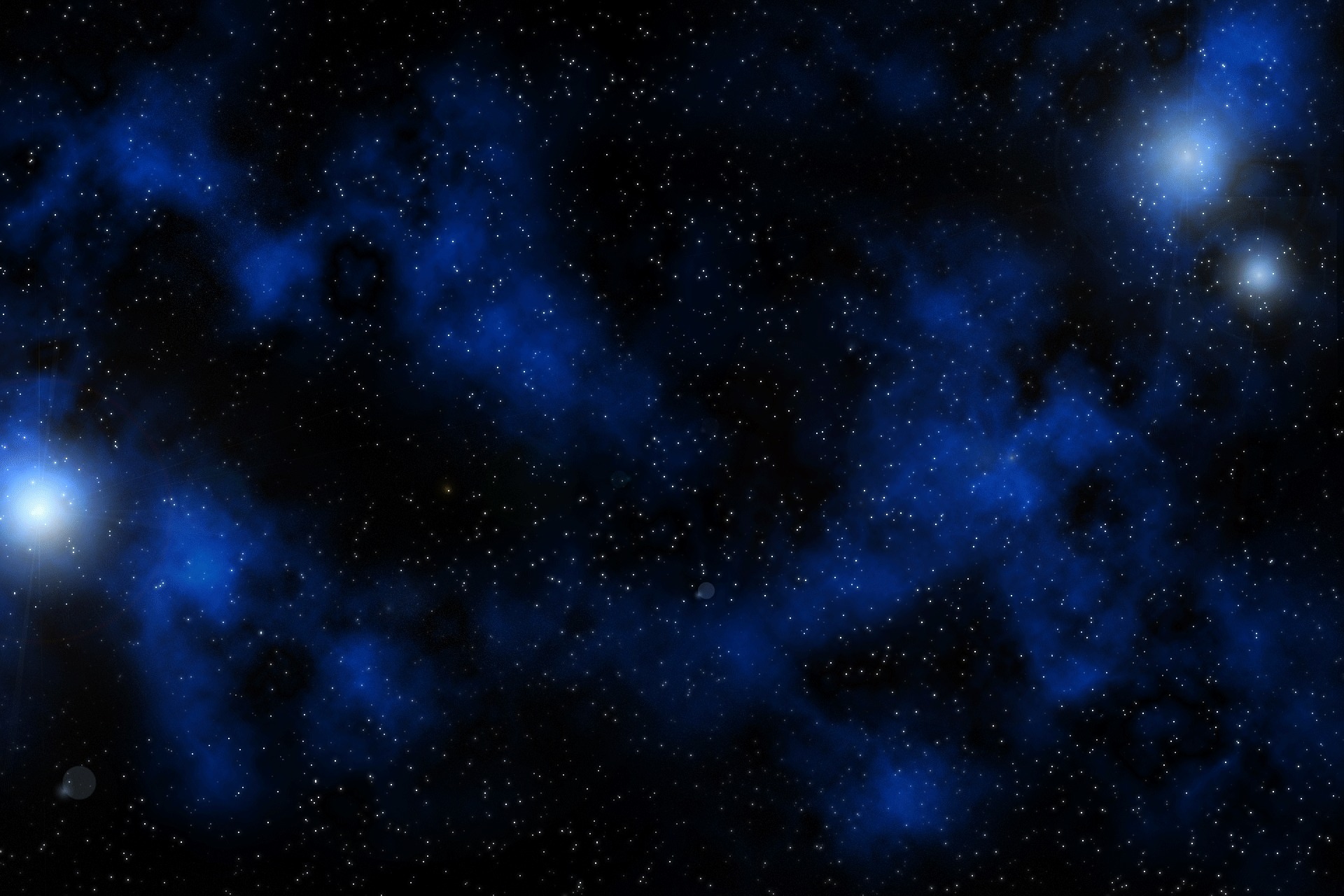
夜常反思。
我前两天上豆瓣找到以前的一个观察对象——有一点观察价值但不会成为朋友也不受尊重的人类——将自己的观察记录发给了他。这一部分内容自然不是好话,说是羞辱也不为过,至少对方表示自己受到了侮辱和伤害。
我认为师生关系偏向于合作关系,或说工作关系。除了学习之外,教师和学生不会产生太多交集,接触学生的心理和生活也不是教师必须承担且有能力承担的责任。尽管存在负责心理课和心理疏导的教师,但她们如同摆设……学生可能不会在遇到困难时想到他们,就算想到并愿意尝试交流,他们也不一定能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。
在书城听了卢一萍的讲座。
他讲了自己的生活和写作经历,从中可以看出这是有个性的作家。
他对父辈的生活很感兴趣,想了解人们在那个动荡的,充满政治风雨的年代如何生存,又如何看待他们的青春、梦想和人生。后来采访湘女就有这种因素,同时也有机缘。当时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,湖南省委宣传部委托人找他,希望他写一个主旋律的作品。但是当他接触到第一个采访对象的时候,就发现他如果按他们的要求来写,他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。所以他就放弃了他们的要求,自己去采访。在整个新疆寻访了4个月,采访了200多个湘女。
看了戏剧《沧浪之水》,改编自阎真的同名小说。
查了原著,发现其中有两处很好的改编,可以叫“发挥戏剧特有的表现力”吧。
一处前情是池大为的儿子被烫伤,他求司机开车送医,被拒绝了,只能求马厅长借车。到医院后,钱不够交费,他到处求人帮忙,最后是一直瞧不起的前同事给面子解决了。
下午去福田图书馆听了一场讲座,《在走和留之间,日子摇曳 ——走近东欧文学》。主讲人是高兴,文学译者,曾经是外交官。
听到些有趣的事情。
《哈扎尔辞典》原来在中国知名度并不高,后来名气变大,是因为一个事件。韩少功出了本书,《马桥辞典》。一次交流会上,有个人口无遮拦,说这本书就是抄袭《哈扎尔辞典》。作者肯定不干,就要打官司,所以这本书就出名了。
今天反思了自己对金钱的焦虑感,发现童年其实受到传统观念很大影响。
从小,我的母亲就说,女人不需要赚太多钱,女人一定会结婚生子,结婚后女人的经济、生活就由丈夫一方负责了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,原来的家庭不会再管女儿的事情。儿子则需要金钱、房产和车辆等作为结婚的资本,以后也主要负责赡养老人,所以儿子会获得长期、全面的支持。
今天去看了OCAT的展览开幕式。展览是关于疫情的,名为“那些……日子”,据说原名是“那些不自由的日子”。听一些人讲完开场白后,我进入展馆看展品。我感觉展览一般,记忆点就是题材。
现场有我认识的人,还有我想认识的人,可是我不敢上前打招呼,只在他们附近看着他们。
下午有演唱会,进行演出的是重D音乐队和西三歌队。开幕前先由重D音唱了一首《春天一定会来临》,然后就是主持人登场了。5点时演唱会正式开始。
从小到大,我最害怕的考试题型就是作文,一碰到作文就犯怵,几乎遇到任何命题都感觉根本写不出来,只能硬编瞎话来凑字数。我的作文分数,大部分时候就只比及格线高一点,偶尔获得较高的分数,还是因为批卷老师大发慈悲。
我所看见的中国,是荒凉而黑暗的荒野。
不幸和痛苦弥漫于盛世的表象之下,而弱小的人却难以发声,只能在现实中孤独地挣扎。
我尝试在这篇文章中同时讨论个人的生命体验与宏观的社会现象,这需要一定的知识和想象力。至于效果如何,就留待读者检验吧。
那么,欢迎来到我的世界。
大约在12-14岁时,我非常骄傲,尽管明面上没有表现出来,但心里是看不上大部分同学的,认为我和他们没有共同话题。但我和几位老师的关系倒还不错,我不时会去找他们聊天,我们的交谈大部分是关于各种问题,那时我是个不折不扣的“问题少年”。
小学时发生的事情,几乎从来没有写过也没有说过,不愿意。整个小学,这段往事始终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之一。不过我的小学生活确实比较乏味。
不写出来也没有什么作用吧,不过是没有别人知道而已,然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
大约是二年级,我和我的同桌不知为何相互敌对。我们的日常就是骚扰、吵架和打架。他一般会拉同学来帮忙,而我不会,所以常常是一对多,不说输得很惨也不可能会赢吧。每天上学都是这样,真是十分精彩。现在很多事情都忘记了,写几件我还能记得的事情吧。